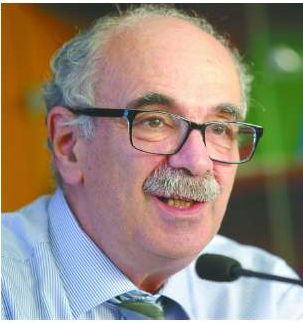【核心提示】如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,即西方国家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模式上已失去其霸权地位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已放弃发展社会科学,而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已经取代其统治地位。当下,需要我们从全球化的视角对社会科学进行再思考。
迈克尔·威维尔卡(Michel Wieviorka),国际著名社会学家、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主席。曾任国际社会学协会(ISA)主席、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运动与社会干预研究中心主任。 社会科学发轫于西方,始于英、法、德,然后进入到美国,从而开始具有一种普遍性,随后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陆续得到发展。但如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,即西方国家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模式上已失去其霸权地位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已放弃发展社会科学,而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已经取代其统治地位。当下,需要我们从全球化的视角对社会科学进行再思考。 重建社会科学的“普遍价值” 全球化背景提出了两个反思的路径。第一是对社会科学的西方中心论的反思,我们是不是在方法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,太过受到西方世界的影响?是否应该重新思考西方社会科学与思想文化传统的关系?第二是对社会科学应用范围的反思,社会科学是不是应该具有更普遍的价值? 按照相对主义理论,中国、韩国、法国的思想是无法沟通的,比如中国的思想首先是被中国人所接受,其次才能被韩国人接受,最后有可能被法国人接受,因此,各国思想并不具有普遍价值。对此,我坚决反对。需要强调的是,西方所谓的普遍价值,正如马克思所言,是非常抽象的,往往与现实相距甚远,并经常成为殖民、剥削等行为的工具。所以,现在尤需思考的是,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,应如何重新对“普遍价值”进行一种再创造。 1950—1990年代:从系统化转向碎片化 1950、60年代的社会科学与今天有怎样的区别?以社会学为例,在1950、60年代,社会学不但具有介入性、政治性、公共性,而且带有很强的批判性。当时的社会学家往往拥有非常系统化的理论和思考方式,能够以一种全面的视角来思考问题。比如,1950年代的社会学家帕森斯就非常热衷于建构庞大的社会理论体系,并进而以全面、系统的视角来思考社会学问题。帕森斯建构的这种宏大体系同时继承了马克斯·韦伯和涂尔干的思想传统和理论资源。当时的社会学家虽并不全是功能主义者,但大多能以较全面的视角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。 在1950、60年代,具体的分析与宏大的思想体系是可以建立联系的,而且社会学家可以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转换。1950、60年代甚至70年代初,社会学家不但对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具有很强的介入性,还会参与到一些社会运动中。例如在法国,当时的学者借助马克思主义抨击政权而非仅仅服务于政权。 那个年代社会科学的另一个特点是结构主义甚嚣尘上。虽然当时的社会学者比较多地介入公共生活,但是与此矛盾的是,占主流的结构主义认为“主体”是非常危险的。当时的研究往往致力于从结构上理解制度、体系等抽象事物,对行动者并没有多少兴趣。当时的社会学者因为要介入公共生活,也需要和其他领域的公共学者进行接触。比如,在作为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中心的巴黎南泰尔大学,与社会学家一起工作的是研究城市化、建筑以及从事精神分析的学者。 1970年代,社会学开始活跃,主要思潮也发生巨大转变。社会学者开始质疑功能主义这样的宏大体系,诚如舒马赫所言,“小的就是好的”。学者们开始关注非常具体的相互作用关系,功能主义完全失去势头,对于帕森斯的作品,学生们可能认真读上两三页都很困难。 而到了1980、90年代,学者们认为应该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,随处可见社会科学研究碎片化的现象。有些学者很快理解了这一转变:古德纳在1970年代的《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》中,描述了功能主义是如何走向没落的;美国社会学家霍洛维茨在《社会学的解体》中批判了社会科学的碎片化和相对主义。社会科学的碎片化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。那时,在美国大学附近的书店里,社会学专栏中几乎所有的书都落满灰尘,书的种类和数目也乏善可陈。但有关同性恋、大屠杀和非裔研究的书目非常多。这种碎片化,说明社会学实际上已解体为多个不同的领域,而这些领域间并没有共同的理论。可以想象,社会学的碎片化必然会导致相对主义的出现。每个人都是自己研究领域的专家,在各领域间并没有交流的必要。 以“全球”、“个人”取代“系统”、“行动者” 1990年代之后,社会科学经历了新的变化。如今的社会科学需要探讨两个相互对张又彼此关联的问题,分别是全球化和个人主义。全球化是一种全面、广泛的问题;而个人主义则是具体、个性化的问题。经济的全球化弱化了组织和机构的作用,使国家的功能发生改变,并使每个人都能在扩大的活动空间中做自己的事。全球化同时也弱化了社会团结的作用,弱化了群体集体行动的功能。因此,可以说,全球化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。 个人主义究竟指什么?可以从两个层面探讨。第一,个人主义指的是维护个人的利益,这是最直接的一种看法,个人为了收入、工作,以及获得更好的教育或医疗来使自己能够更体面地活在这个世上。第二,个人主义指涉一种个人自我建构的忧虑。许多社会学家使用“主体性”来描述个人自我建构的能力。于是,一方面全球化越来越深入,而另一方面,个人主义趋势也日益明显。 但是,不可能所有人都能获得最大利益,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能获得主体性。贫困、种族主义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等不公正、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。一个人如果不能成为自己行动的主体,就往往会转而产生另外一种倾向,如暴力种族主义。我们在面临全球化的同时要对个体进行一些非常具体的思考。在1960、70年代,就有社会学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,如米歇尔·克罗齐埃在《行动者与系统》中所表达的。另外,赖特·米尔斯在《社会学的想象力》中批判了功能主义,认为应该把微观个体困扰与宏大历史、结构分析相结合。所以,现在就不应该仅限于从单一社会或民族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,而应该把思考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空间,即全球化背景下。这就意味着之前所说的“行动者”和“体系”已经不成立,应由“个人”和“全球”视角所取代。这与社会学最初诞生的民族国家背景完全不同。 (本文根据威维尔卡教授2013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;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汪建华/整理,李培林/审定)
|